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2025年10月31日下午4点在北京798第二空间呈现袁运生的大型个展“失序与并存”。此次展览由崔灿灿策划,是艺术家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的首次展览,呈现其跨越五十余年漫长艺术生涯的创作与实践,涵盖了30余件布面油画与纸本作品,以及10余件瓷盘画。
袁运生艺术的几个切片
1
1979年,袁运生结束了十几年的下放生活,回到北京参与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这一年也因为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中国美术史上被画上浓浓的一笔,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历史也依据这张名作画出了分界线: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生命的束缚与生命的解放。
在袁运生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他创作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例如云南白描、机场壁画、表现主义,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国现代艺术和民族艺术的转折点。也由于其重要性,传奇的一生,袁运生的作品和公众形象持续引发着人们的讨论,艺术史学者和艺术家一次又一次的回归他的作品。
然而,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并非着眼于对这段显赫的历史的刻画,而是试图寻找在这个标志性时刻前后的发生:那些细微的铺垫、缓慢的前奏和之后的故事,看似“无关紧要”的时刻。作品时间的标尺也来到1979年前后的几年。
1970年初,袁运生创作了一系列静物与风景作品。那时,他还在长春,社会仍处在紧张的关系之中,现实主义的主题创作占据着绝对主流的位置。他画中绚烂的色彩,“无关紧要”的生活主题,与当时的主流显得格格不入。一张名为《磁州窑瓶花卉》的作品无意之间显露了几个信息,一是袁运生个人对印象派和现代主义的语言,保留着浓厚的兴趣。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器物有着独特的情感,在对磁州窑瓶的纹饰刻画上可见一斑。三、他对生活充满热爱,即便是细微的花朵都被赋予生命绽放的歌颂。同样的案例,也在《长春植物园》中出现,支架上的藤蔓,散发着自由而又不羁的生命力,仿佛那个时期他在困境中的阳光,成为个人生命和自由欲望的写照。
 《磁州窑瓶花卉》,布面油画,60 × 73 cm,1975
《磁州窑瓶花卉》,布面油画,60 × 73 cm,1975 《长春植物园》,布面油画,56 × 78 cm,1971
《长春植物园》,布面油画,56 × 78 cm,1971 《长春南湖公园》,布面油画,59.5 × 69 cm,1972
《长春南湖公园》,布面油画,59.5 × 69 cm,1972
1972年,长春的夏天来临,北方漫长的冰冻期在春天之后悄然结束,那景色像极了袁运生心中的渴望。在《长春南湖公园》中,他描绘了人们在公园中游泳的场景。画中的题材与印象派的语言逐渐同步,不再是对简单风景的刻画,而是描绘如马奈、修拉笔下日常生活的场景:人们在湖中玩耍,恋人在船上约会,家庭在公园里享受一天。这是中国1970年代中少有的对现代生活的描绘,也是中国人少有的城市、公园与假日的闲暇。
1978年,社会的冰封已然松动,出版业也终于迎来了专业出版的契机。这一年,袁运生应云南美术出版社的邀请,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写生。三张云南写生系列为我们呈现了“机场壁画”的前奏,那些民族特色的服饰,层层叠叠的衣纹,傣家人的歌舞与节日,既满足了袁运生曾经对现代艺术的想象,又成为中国线描的最佳载体,召唤着新的表达手法和寓言故事的来临。
其中一张《云南植物写生之三》,为我们显露了袁运生“在地性”创作的特点,他如何向植物、雨林和自然学习,并在其中建立精神性的生命隐喻。繁琐而又复杂的根茎、枝叶,丛生的交错结构,为我们呈现了雨林中万物互联的世界。
 《云南植物写生之三》,纸本钢笔,28 × 109 cm,1978
《云南植物写生之三》,纸本钢笔,28 × 109 cm,1978
画中的生长,又仿佛为我们提供了在“机场壁画”诞生之前,袁运生在整个70年代工作方法与创作路径的隐喻:首先,像是一棵倒立的树,植物细微的枝桠,由那些不同风格的碎片化探索组成;其次这些“无关紧要”的多样化探索,吸收的阳光反馈给树茎,树径逐渐粗壮,引向根部,造就了个人的独特风格;之后,借助土壤中的水份,历史的给养,对于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袁运生象征着现代性和民族化的“机场壁画”才会来临。
2
一张声名显赫的名作既奠定了艺术家的地位,也无形之中形成了人们对风格的固定印象。
1979年,人们被袁运生“机场壁画”中优美又富有节奏的画面所吸引,它似乎成为艺术家风格的象征。然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他总是多向的、立体的,有着内部的生命张力。1980年,袁运生为我们呈现了在“机场壁画”之外的张力,那些狂野的、不羁而又自我反叛的生命力,他生命中另一种炽热的阳光。
1980年的《爱恋》、《生命之歌》,和大型壁画的反复推敲不同,它们显现了一个更为放松、自由、恣意的艺术世界。说是轻松,十几个彩绘的瓷盘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像是一气呵成,尽兴地洋溢着他的才华。“速度”总是能抵达意外,也能最大程度体现潜意识中流动不定的闪念与灵气。
 《爱恋》,纸本彩墨,101 × 101 cm,1980
《爱恋》,纸本彩墨,101 × 101 cm,1980
 《生命之歌》,纸本彩墨,104 × 100 cm,1980
《生命之歌》,纸本彩墨,104 × 100 cm,1980
这些瓷盘与毕加索、马蒂斯的创作如出一辙,它们都是生命在造型、色彩和构成中自由与狂野的律动,也是追求想象力的开始。某些方面,这些创作于1980年的作品,亦为我们表明了袁运生早期的艺术立场:1、生命力是不分地区和民族的;2、艺术是无国界的,既可以在西方的现代主义、立体主义和野兽派中寻找灵感,也可以在中国传统壁画、水墨中找到启发;3、材料和媒介是可以自由切换与运用的,无论是壁画、油画、纸本,还是陶瓷、水墨,都是艺术家自由创作的载体。
生命的张力,并不只是优美的,它有些时候需要放弃自律,直面痛苦、扭曲与暴烈。两张水墨作品《少年》与《相思》,呈现了袁运生艺术的另一面:生命力的躁动与不安,情欲在艺术中历来的苦苦求索与痛苦折磨。这两张作品也成为袁运生之后代表性的水墨作品的早期写照,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一个属于表现主义时刻的袁运生,而画面中所暗藏的那些表现与抽象、传统与当代、民族与西方、个人情感与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也将在80年代、90年代全面爆发。
这个展厅中唯一一张创作于2015年的新作《怜爱》,作为结果,悬挂于高处,注视并等待着一切的发生。

《少年》,纸本水墨,137 × 68 cm,1980s

《相思》,纸本水墨,137 × 68 cm,1980s

《怜爱》,布面油画,400 × 250 cm,2015
3
1982年初,袁运生去往美国。出国前,他发表的文章《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表明了他多年来对艺术与个人、民族、国家关系的思考,文章中的观点亦内化为伴随他一生的经验和使命,与他即将到达的美国之间,时时对立与作伴,构成一个可以跳脱西方,进行观看的支点。
这个单元以一张1980年的《失序》作为开篇。那时,袁运生仍未出国,画中立体主义和塞尚的痕迹相互交织。失序的感受,像是彼时国内印刷模糊的出版物上刊登的画作。那时,西方的原作在1980年的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艺术家对西方艺术的理解,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碎片。对于袁运生而言,对西方的深入了解到了美国才真正完成。从了解到认识,再到反思,袁运生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立体的角度来完成。1982年,袁运生探访了徳库宁、贾斯珀·约翰斯、乔治·西格尔、罗伯特·劳申伯格等几十位艺术家的工作室,这也让他对画作背后,艺术家的思考动机与观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袁运生也成为第一位与西方战后艺术进行直接对话的中国艺术家。
 《失序》,布面油画,107 × 117 cm,1980
《失序》,布面油画,107 × 117 cm,1980
在美国时期,袁运生也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大量的原作和系统性的观看,为他提供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的完整认识。他可以分门别类的去研究,研究构成现代主义的条件与语言,并逐一思考或是实践。三张创作于1985年的素描草稿,呈现了他对线条与叙事张力的反复研习与创造;两张1990年的色粉画,显现了他对韵律、节奏与色块穿插的实践。也是基于这些细致化的实践,我们发现,同样有着现代主义色彩的1994年的《神殇》,相比1980年的《失序》,是如此“原汁原味”,那种老练与地道,像是西方大师的手笔。
创作于1989年的《时间》、《人世》、《九重》,是袁运生将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进行结合的典型作品,也是他美国时期个人风格的成熟。在这3幅作品中,他绘画视作不同的行动,表达内心不同的精神状态,强调过程、材料、质感自身如何生成故事的重要含义。然而,对于袁运生而言,出国前写就的《魂兮归来》一直为他提供着可以跳开的支点:在贴近西方现代主义同时,又能时刻以华夏文明进行嫁接与反思的多重立场。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在作品的命名中,似乎可以找到明证:“九重”以东方的多重宇宙观,比拟西方绘画中的色层与色块的叠加;“人世”以中国人世界观,来比喻画中生命的飘荡与沉浮。
 《时间》,纸上综合材料,180 × 194 cm,1989
《时间》,纸上综合材料,180 × 194 cm,1989
某些方面,袁运生的创作又是迂回和循环的,他不断以东方凝视西方,以西方创造东方。他的观点也总是随着认识而改变。1970年代,他渴望现代主义对自己和这片土地的解放,80年代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艺术的结合之中。他过往的作品也总是被反复的搁置与修改。一张名为《爱慕》的作品,创作于1991年-2015年,在漫长的24年间,他的“认知”不断改变着“认知”,他的“向往”也不断修正着“向往”。
 《爱慕》,纸本彩墨,107 × 106 cm,1991-2015
《爱慕》,纸本彩墨,107 × 106 cm,1991-2015
或许是袁运生作品中总是流露出炽热的创作欲,我们总是忽略他在艺术理论上的重要建树,他的写作、宣言与观点对中国美术界的影响。从赴美之前,他的文章《油画民族化?》和《魂兮归来》,到他之后对墨西哥壁画如何凝结了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毕加索、马蒂斯、波洛克如何植根于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又在何种情形下借助了民间艺术的力量。这些对于西方艺术家人生传记和生命历程的了解,无不激励着袁运生自己的艺术人生与道路,而那些传奇性的故事与画作一起成为所有艺术家可以分享的宝贵财富。
4
一直以来,“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成为袁运生艺术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创作于2001年的《饕餮》与《牌局》,为我们揭示了袁运生创作的多维度和复杂性。在这两张有着明显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中,袁运生表达了他对美国生活和消费主义的看法,那些有着都市特征的纸醉金迷的场景,描述了现代人的欲望,狰狞而又扭曲的人物,臃肿变形的身体,仿佛在争夺着某些事物。这些极具张力的画面结构,赋予了现实某种戏剧性的色彩,成为独属于袁运生的一种“魔幻现实主义”。
 《饕餮》,布面丙烯,152 × 351 cm,2001
《饕餮》,布面丙烯,152 × 351 cm,2001

《牌局》,布面丙烯,152 × 351 cm,2001
或者说,在袁运生的这两件作品中,他仍保留了对现实与时局的观点。美国的生活,不仅塑造了他的艺术语言,也使得他重新去思考那些西方现代生活自身的困境。某些方面,这些“困境”也从侧面回答了袁运生对人的处境的关注,道德和故事在其作品中的重要位置,以及表现性和戏剧性的手法,如何激活了现代主义的形式困境。
5
在展览的最后一个房间,我们展出了袁运生两个系列的作品,一组是90年代的纸本水墨,一组是新近的布面油画。这两组作品为我们显露了艺术家始终的宿愿,从民族化走向文明的自觉,以寻找人类共同体中的“中间地带”。
同样,借助这两组相隔20多年的作品,我们试图展示一种对比:多与少,加与减,昂扬与宁静在袁运生艺术历程中的交织。从最直观的感受看,90年代初的水墨作品仍是在做加法,仍是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绘画在艺术家那里的缠斗。虽然,画面中的线来自于中国传统,但却有着超越传统文人的强劲能量,错综的线,在画面中不断地繁衍,蛮力般的生长。袁运生试图用表现主义充满张力的灵魂,昂扬的姿态,去打破中国山水画在用线时程式化的师古和对欲望的束缚。
而在2017年的新作中,线条被有意的收敛,繁杂的情感也在山水中被克制。晚年的袁运生,似乎少了一些包袱,他不再用色彩或是繁多的线条,将整个画面胀满,而是有意的留白,呈现某种“未完成感”。人生的暮年,袁运生好像回到了更遥远的过去,回到1981年西行中,他所看到的那些传统造像里寥寥数笔的线条,那些山水、岩石、远江中的诗意。“民族化”和“文明”的宏大词汇,或是“第三条路线”所暗示的对抗性,也在画中一并淡然。一辆小火车,在山峦之间穿过,违和之外,却多了一种天真烂漫的想象力与童趣。亦如他所钟爱的毕加索的人生,在晚年摒弃早期复杂的手法,回归到最基本的形象与主题,那些象征着西班牙文化的鸽子、斗牛与猫头鹰。
 《无题》,纸本水墨,206 × 220 cm,1990-2016
《无题》,纸本水墨,206 × 220 cm,1990-2016
如今,即便与袁先生有过几次合作,我仍然好奇出生于1930年代的艺术家,在那个民族积弱的年代里,他们个人的命运缘何与家国天下、魂兮归来紧紧绑定,他们又为何始终兼具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与一笔负千年的重任。袁先生一篇名为《当代西方艺术随感》中,道出一段朴实而又真挚的感受:“我对中国艺术的前景寄予希望,虽然这将是个过程,但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不应总跟着人家后面走。”
或者,为了让这份理解变得亲密,我换一句袁先生更为轻松和童真的话语,结束这篇文章:“先回到源头,在自己的文化里润一润、泡一泡,滚一身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长一棵芽,雨露,那是甘露,亲切、温暖、值得。”
展览信息:
策展人:崔灿灿
2025.10.31 – 12.10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二空间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236977919@qq.com。发布者:admin,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stm.com/news/1410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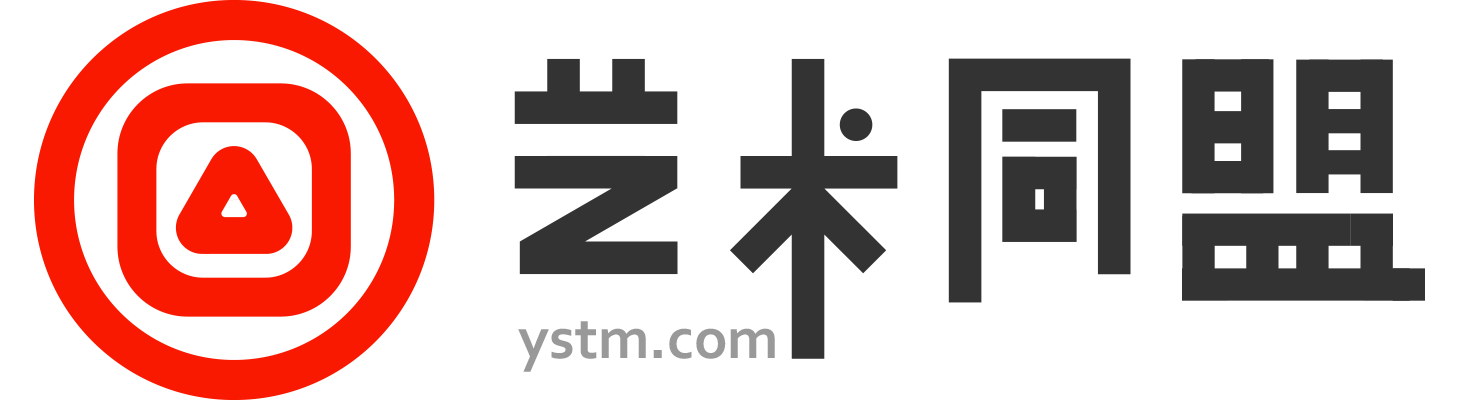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