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 庸置疑,毛焰是画家中的画家,现存关于他的写作多如牛毛,但你会发现除了与他熟识的知己文人和画家——如韩东、何多苓——的评析之外,极少有文字能够冲破那层包裹在这位画家身上的天才叙事和光环,切入毛焰施展于画布上的技艺。鲜有作者能够恰如其分地为读者照亮一条观看之道,说清他那些晦暗混沌的画面深处蕴藏着的巨大引力从何而来,这位不从属于任何趋势潮流的画家又究竟是如何超越不断裂变的美学分歧而获得普遍认同。
今年九月,毛焰迄今最大的个展在松美术馆开幕,展览由毛焰曾经的学生崔灿灿策划。90年代,毛焰从北京迁往南京任教,新千年之初,崔灿灿成为毛焰在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学生,2012年,崔灿灿从南京搬到北京,开启了作为策展人的职业生涯,十一年之后,这对师生的轨迹在这次毛焰的同名展览中再度交汇。展览以从毛焰创作中抽取出的四幅迥异的画作开篇,十三个展厅切片式地展出了毛焰跨越二十六年的近百件作品,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崔灿灿强叙事性的个人策展风格,呈现出有关艺术家创作的万千“偏见”之一种。奇妙的是,漫步于充满理性气息的方正展厅,毛焰那些不同灰度的画面仿佛涌动着另一种更为激烈的言说,那些被统称为“绘画语言”的内在线索时而聚合纠缠,时而破碎消隐,牵引着观者的脚步不自觉地偏离展厅规划的观看节奏,进入到或如崔灿灿所言及的,由画家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所构筑的差异时空。本文作者王紫薇与崔灿灿的对话从毛焰个展的策划谈起,在对艺术家的细读中延伸出当前生态下的个体映照和他对争议性话题的回应。
王紫薇:我们先从展览的整体策划谈起吧。为什么说这次展览不是回顾展?假如策一个毛焰回顾展,和这个展览的区别会在哪里?崔灿灿: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指标,首先, 1997年之前的作品我们没有展。例如毛老师曾经最广为人知的《记忆的舞蹈,亦或黑玫瑰》等。回顾展很容易做成一种反向发明,就是把一切进展都解释为合理的,把每一个过去都理解为是预埋了伏笔,暗示这个艺术家一定会朝着某个方向走。这个展览选择以97年作为开端,其实呈现的是和97年之前的断裂性的差异,虽然毛老师在90年代的作品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来,他真正开始进入到个人的绘画语言系统的搭建,差不多是从97年开始的。

毛焰,《记忆或舞蹈的黑玫瑰》,230×150cm,1996,布面油画
王:为什么以《我的诗人》为起点?崔:从《我的诗人》开始,毛焰进入了对肖像的深入研究,因为肖像画是一种很容易被工具化的形式,用于表达题材、精神、社会和时代。中国当代艺术这么多年,肖像画一直在一个题材的更新的状态里,90年代发生了什么,艺术家就画什么,2000年之后发生了什么,艺术家就又画什么,似乎题材是作品成立的一个重要指标。包括90年代我们写文章每每都要讲到时代大背景,但是在时代大背景之下,仍然有人与时代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可能恰恰是个人性所在。
艺术的表达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艺术和时代的必然关系,另一个是我们是否能缔造更好的工具来精准地表达?有时候工具的更新要比题材的更新更重要,《我的诗人》是毛焰更新这个工具的重要节点。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尝试放弃中国当代艺术叙事中惯有的对题材变化的关注,寻找一个个人的路径,探讨艺术家如何更好地接近题材。这样的话艺术就不仅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证据,也可以作为个体调节自身和艺术、时代关系的一种方式。

毛焰,《我的诗人》,61×50cm,1997,布面油画王:的确,跟与他同代的那批在北京的画家相比,比如说走向政治波普的那一批,毛焰在创作方向上有很大的偏离。《我的诗人》是在他去到南京之后创作的,他当时进入了一个诗人和导演组成的文艺圈子。崔:在97年之前,毛焰描述的是年轻人普遍的迷茫,这种迷茫可以理解为类似美国“垮掉的一代”,也和当时方力钧他们画“玩世主义”有相似之处,但是到南京之后,毛焰开始画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比如说他画的李小山和韩东,那是他个人最早开始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而这并非一个普遍的社会困境。《我的诗人》描绘了1997年韩东的精神状态,它是文学史和艺术史的一个经典的交汇。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张画之所以动人,并不仅仅因为画的是韩东,更因为它体现了绘画描述本身的精彩。

毛焰,《小山的肖像》,170×100cm,1992,布面油画
所以从《我的诗人》开始,毛焰进入了对绘画作为工具的探索。直到“托马斯”系列出现, “画的是谁”这件事已经不再重要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当代艺术非常强调对政治符号和社会现实的描述,我们希望每幅肖像都是时代的一颗结晶, 毛焰却在“托马斯”系列的创作过程里走向了传统肖像绘画的反题,用漫长的时间去描述一个无关紧要的、和中国经验、符号、现实毫无关系的人。面对中国的现实转变,艺术家其实大多是应接不暇的,今天的中国这么内卷,每个人都试图快速地获得一个结果,一条短视频三分钟不嗨就会被刷过去,有多少艺术家愿意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做实验?毛焰刚开始画托马斯的时候,很多人并不理解,觉得毛焰怎么突然画一个跟我们没关系的老外,但事实上它的意义可能在很多年后才会显现。

松美术馆“毛焰”个展现场王:你过往策划的艺术家个展很强调大的外部历史,但这次反而格外关注艺术家工作方法的内部变化。崔:做毛焰的展览,我面对的第一个命题就是时代这把标尺的失效。我们今天如何对时代作出反应?一种方式是把时代理解为一场暴风骤雨,时代迅速地畸变,我们也要迅速地畸变;另一种方式是逃离时代对我们的塑造,自觉专注地去塑造一个比时代更恒久的个体。呈现毛焰的专注是这个展览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它要对照的是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卷现状——我们如何不去上海?如何不去香港?如何不生怕自己不在场,而是在工作室里一点不心慌地工作?

松美术馆“毛焰”个展现场
王:但同时毛焰也是一直以来被天才叙事裹挟的一位艺术家,你在做他个展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去处理或者回避这一点吗?崔:毛老师不是个天才,那是媒体的话语,天才是随时可以被剥夺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奋、专注、努力,在自己的体系里不断燃烧。大家总说毛焰1997年那张《我的诗人》画得好,可是你想想,那个时候他在南京的精神状态会是好的吗?难道刚开始画托马斯的时候他没有迷茫吗?笃定不是一瞬间达成的,而是在一次次和迷茫的抗争之中达成的,这是一种很细腻而又丰富的情感。这些年艺术家策划个展,晚上看艺术家资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如果是我,在那个年代会如何选择人生?真的全是正向选择吗?名人在忆苦思甜的时候常常反向发明,不断把自我合理化,但其实自我满是焦灼不安和困境。

松美术馆“毛焰”个展现场
毛焰经历了十几年的托马斯,才能做到今天的游刃有余,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是面镜子,我既能看见他,也能看见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在展览的开篇,我用了四件作品勾勒出一个疑问,打破线性的叙事。否则假如观众看到第一个展厅是90年代末,第二个厅是2000年初,这个时间轴会带来一个问题,观众会沿着它去理解艺术家创作的所谓正向推进。但我希望呈现的是毛焰作品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引导观众看他是如何进两步退一步、进一步退两步。
王:我看到过一张托马斯跟毛焰一起出现在朱文的片场的照片,他也是毛焰所在的南京那个文化圈子里的一员,既然对象不再重要,是不是对于毛焰来说,其实画托马斯跟画韩东是一样的?崔:不太一样。韩东他就画了两张,在捕捉经典瞬间,和摄影一样,在肖像里面,人们总是试图捕捉决定性时刻。对于“托马斯”系列,毛焰从前几张画中找到了决定性瞬间,但当他画将近一百张托马斯的时候,他面对的是画重复的一张脸,如果让它产生变化,唯一的方式便是语言的变化。

(左)毛焰,《托马斯肖像 2004.No.5》,75×60cm,2004,布面油画;(中)毛焰,《小托马斯肖像——白眼》,36×27.8cm,2009,布面油画;(右)毛焰,《托马斯肖像 No.1》110×75cm,2016,布面油画

毛焰与托马斯在朱文电影《小东西》拍摄现场,2008年
王:“托马斯”系列对于观众来说也或多或少是个迷,在创作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毛焰的画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具体转变?崔:从“托马斯”系列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征上的变化,就是毛焰开始进入到灰色系列,色彩在他的作品里面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限度。另外更重要的是经过“托马斯”系列,毛焰从一个主题性画家转变为语言性画家。

毛焰,《H的肖像》,61×50cm,1999,布面油画
肖像画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再现的传统,古典肖像绘画着重表述对象的意志、道德、权力、荣耀,到了现代主义,对象是一个身份问题,比如刘小东早期的画是典型的90年代开始的一个底层叙事,张晓刚、王广义的绘画是一个比较明确的符号叙事,它们是关于中国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一个精彩描述。在今天多元化的语境下,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描述的对象,但是在90年代末,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所谓的肖像的前卫和一个对象的前卫,对象决定了你所描述的命题是否具备当代性。
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语境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叫“力求明确的意义”,是94年易英写的一篇文章,简单说就是问你是什么?你要表达什么?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但当毛焰在90年代末开始画托马斯,是不是当代、是不是中国、是不是风情,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他想画一个身边的老外,而这个老外对当时的语境来说没有任何符号和意义价值,而且如果你见过托马斯,你会发现他甚至长得也不是那么奇特。就是一个这样的西方人,毛焰试图在他固定的脸庞里寻找一种语言的变化。

毛焰,《托马斯》,50×61cm,2000,布面油画所以我觉得对毛焰来说,通过托马斯搭建工作方法,将过去的肖像里面核心的要义去除,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他后来去苏格兰驻留,画了一段时间的肖像,又短暂回归到对人物的决定性瞬间的捕捉。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托马斯这一个系列,直接从《我的诗人》进入到苏格兰系列的话,画面会是另外一种质感。

毛焰,《椭圆型肖像——珀西·穆斯格劳 No.2》,72.5×53.5cm,2010,布面油画王:你从毛焰这么多年的创作里梳理出了一个几乎是过分清晰的线索,如果他经历了消解肖像的工具性和主题性,继而从漫长的重复中锤炼绘画语言的过程,并走向抽象绘画,那么在这个叙事中,艺术家绘画语言的搭建和抽象之间仿佛存在着某种等同关系。崔:毛焰并非走向抽象,而是并行地发展出抽象这一条线索。当抽象系列出现的时候,对毛焰来说,它一方面是一个独立的题材,另一方面这个题材又重新反哺了他的肖像,这是一个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多重路径解决自己要面对的绘画语言和绘画意义的问题。诗歌也是他现在的创作和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诗歌是对某种意向的捕捉和锤炼,它重新打磨了毛焰捕捉细节感知的能力。

松美术馆“毛焰”个展现场
毛焰,《已凝结或漂泊的 No.2》,150×100cm,2021,布面油画
王:近年来做了这么多艺术家大型个展,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崔:做个展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阅读。我觉得一个策展人的阅读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是对文本知识的阅读;另外一部分是现实感知,人总是在现实的流变中不断获得新的感知,透过这些感知,我们把文本阅读进行内化;第三部分是对艺术家的阅读,阅读他的作品和相关的档案资料。对艺术家的阅读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艺术家个体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策划这个艺术家个展的时候,他跟你讲了一个关于艺术的偏见,你非常兴奋地研究了这个偏见,并且笃信这个偏见极为重要,但做另一个艺术家个展,另一个艺术家又告诉你,我还有另外一套偏见。
所以对我来说,做艺术家个展起到了不断自我校正和自反的作用,我的自反不是在家里自己完成的,是靠实践来完成。王:有多久没做过实验性的项目了?崔:三年了。王:最近这一两年会有自我重复的感觉吗?崔:会,而且我也没法把这种重复美化,确实有时候会感觉到困境。不过疫情之后我出了两次国,一次去英国,一次去俄罗斯,还是补充了一些营养的,我就像一个3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回来重新去看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王: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展览吗?崔:前不久在Tate Britain看Sarah Lucas的个展,我就意识到艺术家的直接经验可能有些时候比文本更重要,我一个作品介绍都没看(别的展览我需要反复使用谷歌翻译来阅读展签),就觉得展览的冲击力足够大。

Sarah Lucas个展,Tate Britain,伦敦王:因为作品本身特别好?崔:一是作品本身特别好,二是做这个展览的策展人意识到即便我们从事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直觉可能比研究分析更重要,包括策展人知道自己应该跟当下的行业领域产生什么样的互动,建构什么样的主张,呈现什么样的价值,这是值得学习的。除了学习也有批判,比如Hayward Gallery做的杉本博司的个展就比较一般,基本上是从他最具代表性的十个系列中各挑了几件来展,我就会觉得展览不生动,因为它把艺术家塑造成了一个没有困境和徘徊期的成功者。

杉本博司个展,Hayward Gallery,伦敦另外我在莫斯科看到一个展览,展厅里的座椅就是一个板子上面放了块海绵,再用钢丝一箍,就成为一个简易沙发,太省钱了,但它同样发展了一种美学。而如果做Rothko的展览你往往就得用黑色皮质沙发。所以一个展览有特别多的细节和叙事可以看,哪怕是挑选出现在展厅里的材料,策展人也面对着很具体的问题——这个材料是否有文化属性?是否有物质上的意识形态?

莫斯科GES2文化之家展厅里的座椅王:最近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批评声音很多,尤其针对市场表现出的对新生代的狂热,作为去年在松美术馆策划了90后艺术家群展的策展人,你怎么看?崔:我更在乎做这个展览之前的感受,做之前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现象,筹备展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蓄势待发、箭在弦上,在那个时间点,这是应该做的,必须做的。至于今天的市场是什么样,那就是另一件事了。有批评是好事,代表这是一个价值纷争的地带。4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公平的事情,但学术价值和市场之间也从来不是直接的等同关系,警惕市场,但不用被市场的结果绑架,我们的工作的价值不以市场为准。

“断裂的一代”展览海报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流变的现场,过几年可能就会变。90年代“大头”和符号最盛行的时候,大家也批判,2000年之后这种风潮结束了,你会发现它的结束并不是因为批评,而是因为社会结构产生了变化,所以是否能产生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今天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试图让艺术市场自身主动变化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们总是有一种奇怪的历史姿态,一种教条,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它控制着我们,声称只有以某种方式创作艺术才是回到它的核心。
然而我们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经典要去继承,过去我们什么都没有,今天也什么都没有,如果把中国当代艺术40年当作整体结构来看,我们真的为这个世界的当代艺术提供过一种新的价值和范式吗?大部分被误以为是历史书写的其实是短暂现象博弈,历史还没结束,现象在不断涌现,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改变名单,调整比例,提供更多的选择。今天某些东西我不能说有历史价值,但我认为至少捕捉了时代情绪。我做“夜走黑桥”的时候,是2013、14年的一个情绪,如今黑桥的城乡结合部消失了,要硬做一个同样的项目我也做不出来。
就像前面说的,巨变不来自于艺术内部,而是来自于社会结构的激变,在过去的三年,尤其明显。但我不会放弃描述这种改变的时刻,我年底会开幕一个关于南方九省艺术家的群展,它代表了我认为的当下的时代情绪,大量的人离开了北京,在一个非中心地带开展他们的工作,我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南方群展调研和采访现场,2023年王:今年还打算做过年项目吗?崔:不会做,可能会做一个和我父亲有关的展览。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突然意识到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谈宿命,因为宿命会让你心安。对我来说,这一年有太多不可解的事情,我只能和它相处,这个年我比较悲伤。王:你之前说40岁之后不做策展了,现在还是这么打算的吗?崔:不一定,可能提前,可能更晚。我很佩服一些人能提前预定自己一生,他有一个明确的纲领,一直在围绕这个纲领进行。王:毛焰是这种人吗?崔:我觉得他是,他有独特的“偏见”,所以他有明确的自己。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236977919@qq.com。发布者:admin,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stm.com/renwufangtan/404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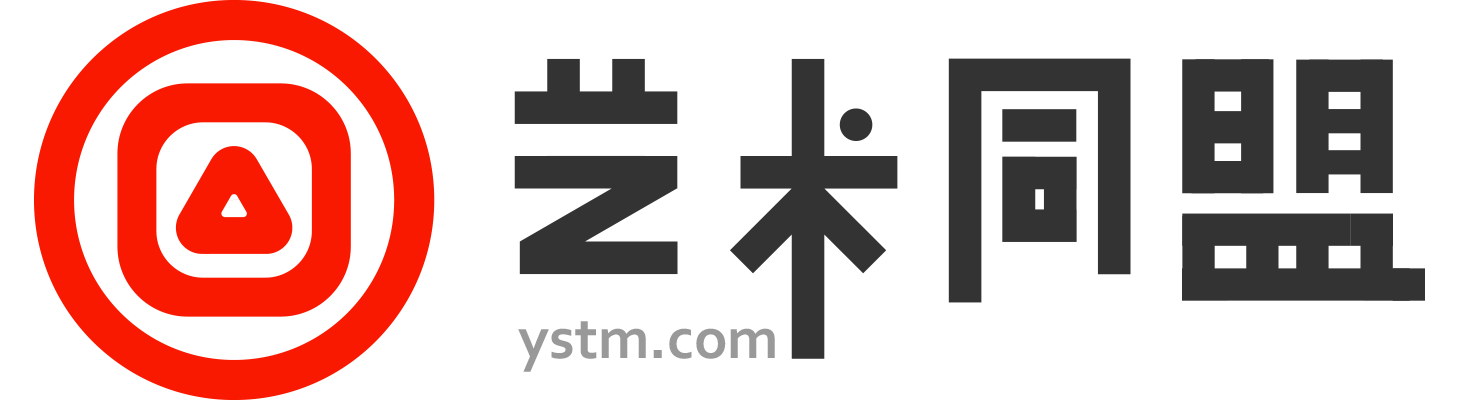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