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海。
曾经有过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海外重要的艺术机构和平台上获得展览机会,意味着被世界关注、被艺术史发现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章节。无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展出的机会,或是参加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群展,都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他们呈现出一种在当地和当下的语境中全新的艺术面貌,也成为当时的世界对今日中国艺术的感性认知。
在后来的艺术史描述中,那是一代人的“出海”,无论是主动或是被动,他们的确是拓展新航线的一代人。他们所经历的戏剧性的历史飞跃,亦是不可重复的一段篇章。这些航线对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艺术家是否依然具有吸引力?在一个经历了全球化几十年后的世界中,在一个互联网实现了全球信息同步的时代,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眼中的大海和世界是怎样的图景?

这张世界地图,对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而言,拥有更多的褶皱和角度。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艺术世界的信息并不闭塞,并不存在一个遥远的“西方世界”。他们离开原地,奔赴大海的另外一边,是因为他们想获得更丰富的视角和更多元的世界,由此可以抵达一个更开阔的自己。
出海曾经是一条艰难但充满承诺的道路,甚至对一些人而言是唯一的艺术道路。而对于年轻的一代,身处多种文化之中可能是一种常态。正如ta们所说:“归属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ta们是在画自己的世界地图。
本次专辑聚焦于几位以不同方式寻找自己大海的年轻艺术家,以ta们的角度来呈现新一代的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ta们之中,有的自小就在数个国家之间迁徙,有的在完成国内的艺术教育之后主动远渡重洋重新寻找创作道路,有的签约了国际画廊获得了新的展示平台,有的在“出海”的过程中收获了真正的自己。这些年轻艺术家所面临的艺术处境和上一代并不相同,ta 们的态度和应对策略也与时代密切相连。曾经的大海承诺了远方的硕果与成功;如今的大海不承诺成功,但一定给予丰富和未知。

张月薇,《勿念(绡蝶属)》(to be forgotten[Ithomia]),
2024年,布⾯丙烯及油彩,180cm×200cm,
图⽚致谢艺术家和柯芮斯画廊
比如张月薇不想被简单归类为 “海外艺术家”,更愿以“艺术家”的身份被认同。她认为真正的归属感存在于跨越文化的理解与创造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是多重文化的载体,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如蝴蝶般自由迁徙。“能进入不同的系统,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由。”

薛若哲,《葡萄II》,2024年,布面油画,40cm×25cm×2cm
对薛若哲而言,探索的是真正进入当代艺术生产的语境。除了打开了眼界之外,最重要的收获是做自己,而不是做“正确”的事情。

余晓,《流光一瞬 No.45,16/06》,2024年,丙烯、油画颜料、
帆布与亚麻布、染色画框、曾用美纹纸胶带、马克笔,32cm×45cm
对余晓来说,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凝视达·芬奇素描的未竟笔触时,她第一次明确感到:不完整并非缺陷,而是一种生成的强度。虽然一开始在海外做艺术和展览,身份标签往往先行,但渐渐她把不同文明的物质观、时间观叠加到了画面结构中,形成一种以切口、折线、镜像为载体的复调语言,收获“视差”。

孙一钿,《自画像》,2025年,布面丙烯、木板丙烯,
左:176.9cm×133.4cm,右:176.9cm×133.1cm,中间:60.1cm×30.1cm,
图片致谢艺术家和施博尔画廊(柏林/巴黎/首尔),摄影©Andrea Rossetti
今年在柏林成功举办展览的孙一钿,用作品正式发言。这个在海外的展览,成为一度身处舆论迷雾中的艺术家的正式发言,是她得以展现真正自我的地方:大家请看作品。她的大海,保护了一个立体和真实的艺术家自我。
我们关注新一代艺术家和 ta 们的大海,是想探索这一代年轻艺术家在世界地图上的新路线。海外留学、海外办展、海外签约、海外定居,这一切曾经是艺术家生涯中的驱动力,如今在发生着怎样的变迁?我们相信每一个艺术家都是独一无二的,ta们的经历可以给后来者新的启发。
你选怎样的海,就会抵达怎样的彼岸。或许在充满流动的未来,每个精神自由的艺术家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地方,而是属于所有ta经历过、吸收过、思考过也深爱过的所有文化之间那片流动的、开阔的地带。
每个人,都在画自己的世界地图。

2012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系三画室毕业后,薛若哲已经在中国的美院系统里面待了8年,在“意识到再待下去只会是无尽的重复”时,她选择了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继续深造。求学期间,她把媒介拓展至雕塑、影像、摄影与版画,由此建立起对“时间—图像”的敏感度。而随后,她在北京、伦敦与巴黎展开长期创作与展览。
在“远航与回归”的叙事里,薛若哲的指针始终指向“时间”。去年,她在伦敦的个展“Chronoscape”(时序之景)聚焦“YYYY-MM-DD”系列。她每天对着花束写生,标注日期,把一束花从含苞到凋零的时序压缩在一张 50 厘米×40 厘米的画布上——这样的尺度,既指向日常,也便于装进行李箱保证每日一画的连续性;而当无法写生时,她便在画面左下角签上日期。她坚持只画“当地、应季的花”,让不同城市的气味、光线和可得性都表现在画布上,时间就得以在层层叠叠的笔触中“存活”,并在旅行、居住、展陈的流动中持续生成。


薛若哲《葡萄》,2024年,布面油画,150cm×100cm
这样的“流动”也延展到身份与叙事的层面。薛若哲的女性人物画则以沉静、克制的笔触,呈现单一人物或少数人物的静态场景,光线柔和却带有幽暗的余韵,让她们既亲近又疏离。在多篇访谈与自述中,薛若哲惯常以“她”来自称:“我相信性别是流动的,使用‘她’也更接近当下我的自我想象与认知。‘画人即画己’,我只能在绘画中一再试图接近我想要的形象与气氛,在绘画中,艺术家是无法掩饰与撒谎的。”
薛若哲在自己展览的布局与观看的秩序中延展这种“流动观”,她在巴黎“MASSIMODECARLO Pièce Unique”等项目中接受“一次只展一幅”的节奏,把作品的更换变为展览的一部分,使“展陈行为”成为时间的外化。这何尝不是在直指薛若哲创作的核心:让作品承认人与经验的可变性,让绘画与时间、性别、旅行共同构成一种连续的现实。

薛若哲《20221119-20221124》,2022年,布面丙烯,50cm×40cm

薛若哲《洛神赋图集—卷一》,2024年,布面油画,250cm×400cm

薛若哲《预备》,2025年,布面油画,145cm×120cm

在杭州的大学美术教室里,余晓第一次产生疑问:当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面貌?自己的绘画创作是艺术吗?除了画布平面内的叙事,还能去往何处?毕业后,她在本地大学任教。在偶然寒假去英国度假时,她在伦敦的遍地美术馆和无处不在的当代艺术中沦陷,却越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需要不一样的创作空间和养分。虽然稳定工作几年,她依然决定辞职赴伦敦进入中央圣马丁读研,寻找到艺术方向,并在毕业十年后,接着在皇家艺术学院进行艺术实践博士研究,并受邀在英国各艺术学院做讲座和导师,以及在罗马 BSR(British School in Rome)国际女性抽象艺术研究会议上演讲。
回溯这种地理上迁徙的原因,余晓说,那是她在一次英国国家美术馆凝视达·芬奇素描的未竟笔触时,第一次明确感到:不完整并非缺陷,而是一种生成的强度。于是,她以“形式性的暴力”撬开画布,把背面的揭示变成图像生成的过程,让观看从消费图像转变为经验的形象结构。

余晓《用单子的循环游戏-致敬法国60年代Support/Surface的艺术运动》,2024年,
画框木条、亚麻布丙烯、折旧遮蔽胶带、LED灯、运输木箱、平头画笔,尺寸可变
自此,材料与图像的迁徙便与她的地理迁徙并行展开:从早年的“抽象水势”与“刚柔并济”的沉思出发,她开始以纸胶带缠绕空间,把原本隐身于制作过程的辅料推到台前;再到近年的切割、折叠与翻转画布,令背面、木框、渍痕与红点等“支撑性残留”成为画面的主动元素。
但是在海外做艺术和展览,身份标签往往先行,余晓的作品容易被归档为“华裔/中国女性艺术家”的范畴。收获在于“视差”的建立:把不同文明的物质观、时间观叠加到画面结构中,形成一种以切口、折线、镜像为载体的复调语言。
在这一代艺术家的坐标系里,物理上的迁徙既是同代人的境遇,也是自我谋求突破的方法。余晓认为,她这一代艺术家的国际化是双向渗透的:既接受西方当代艺术的洗礼,又带着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自信。余晓最近推进的“Da Vinci’s Mirror”系列延续她前几年的系列,令原本隐匿的木框暴露于光下,背面的渍痕、先前贴附的纸胶带、红色圆点的印记,一起构成了画面。这个系列既是达·芬奇的镜像理论,也与中国园林的“移步换景”并置,令作品在现实与抽象之间维持着张力。

余晓《Da Vinci’s Mirror No.60.10/06》,2024年,布面与亚麻布丙烯、
染色画框、使用过的遮蔽胶带,60cm×50cm

余晓《乌托邦瞬间之模因体》,2025年,布面与亚麻布丙烯、
油画颜料、染色画框、使用过的遮蔽胶带,200cm×130cm


展览现场:孙一钿,“浪漫屋”, 施博尔画廊,柏林,2025年,摄影@Andrea Rossetti
2025 年 5 月在德国柏林举办个展“浪漫屋”(Romantic Room)是孙一钿对之前一切喧嚣的回应,无论是支持者或批评者,是旁观者还是幸灾乐祸者。
这是一次郑重的回应。德国的艺术媒体对展览和作品都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去到柏林的藏家们确认了这位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并积极收藏。2025 年 5 月的柏林画廊周是这个城市每个画廊的黄金时节,他们力推的艺术家将在这个舞台上获得巨大的关注。这个发生在德国柏林老牌画廊 Esther Schipper 的展览,让身处舆论迷雾中的艺术家得以展现真正的自我:用作品正式发言。
在这次展览中,孙一钿重组并重构了东西方的图像谱系,在新作中既引用了艺术史的经典图式,又重组了日常消费品和玩具的序列,同时融入了童年记忆、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反思和对艺术史的致敬。这些作品创作于艺术家在顺义的工作室中,孙一钿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室中埋头创作。
出生于温州的孙一钿在读高中时,她的奶奶曾找人算过一卦,卦象符合父母的心意,希望她最好不要远行。于是她没有选择出国读书,而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还去上过两年班。上班的经历让孙一钿痛苦,深知自己只想好好创作。之后的人生是顺利且幸运的,与画廊 BANK 的合作让孙一钿迅速获得关注,然后画廊主马修把孙一钿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柏林的Esther Schipper。
孙一钿踏上国际舞台的道路看似一帆风顺,但命运的每一样礼物都必然有对价。孙一钿自然也有她的功课,被误解、被评论是她的必修功课。潜心工作、潜心学习是她的应对之策。也有过开展前在工作室一边哭一边咬牙完成作品的日日夜夜,她有她的标准和心气。

孙一钿《精品》,2024年,布面丙烯,182.7cm×182.9cm
2023年孙一钿回到校园,在清华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2025 年,在柏林开展,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可。现在谈及去柏林的展览经历,她有幸运儿的感恩和目光。
“有一天,我在德国画廊楼下打车,有个德国女孩突然冲到我面前问我,你就是孙一钿吗?我说你们怎么知道,然后那个女孩就非常兴奋地说她妈妈买了我的拼贴作品。这是一家人,有三个女儿。她们说暑假会来中国学中文,问可不可以到时候去我工作室看看。后来她们来中国,聊天时我才得知她们有很好的家族收藏。”她们加了微信。因为对方只学了拼音,不会打中文方块字,于是她们就时不时用拼音聊天。说到接下来的计划,由于要写博士论文,孙一钿计划专注写论文,短时间内不做大型个展。

孙一钿《送子图》,2024年,布面丙烯,205.4cm×158.4cm

张月薇的人生无法用“出海”二字去形容,她的人生是一场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漫长迁徙。10 岁那年她随母亲离开北京,在肯尼亚和泰国度过童年与青春期,18 岁去伦敦,先后在斯莱德美术学院(Slade)和皇家艺术学院(RCA)完成了本科、研究生的学习,开始拥有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这条独特的轨迹塑造了她独特的世界观:她深知自己的中国文化之根,也不将自己与单一身份的标签相连。
这段跨越三大洲的成长经历,不仅塑造了她的世界观,也深刻影响了她作为艺术家的创作路径。宛如一部流动的地理志,她的作品中是个人迁徙心路的视觉化,像一只蝴蝶,穿山越海,身上带着来自不同地区的花粉。蝴蝶的翅膀,就是一幅它自己的世界地图。
张月薇不想被简单归类为“海外艺术家”,更愿以“艺术家”的身份被认同。她的创作从地图投影、图层结构到蝴蝶意象,都来自于她对身份、迁徙与文化结构的深刻思考。对于她,真正的归属感存在于跨越文化的理解与创造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是多重文化的载体,每一个灵魂都可以如蝴蝶般自由迁徙。

张月薇《勿念(绡蝶属)2》(to be forgotten[Ithomia]2),
2025年,布⾯丙烯及油彩,180cm×210cm
张月薇也不喜欢被简单地贴上“中国艺术家”的标签。“Pilar(她的英国画廊主)从来不会说我是‘中国艺术家’,而是‘艺术家,生于中国’。”她强调,“我确实来自中国,但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已经更靠近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她擅长以双文化甚至多文化的视角观看世界——“我可以读写中文,更流利使用英文,我能观察到中西方媒体和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断层,这是一种优势。”
她的作品常常处理“重复中的差异”“地图与投影”“图层与视觉结构”等议题,看似抽象、几何,实则深深扎根于她对身份、迁移、文化错位的思考。近期她频繁使用“蝴蝶”这一意象——尤其是那种需要经历四五代才能完成迁徙的蝴蝶——作为自我隐喻。“它们的迁徙是写在基因里的。这很像我自己与母国、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张⽉薇:匿径”展览现场,
阿那亚艺术中⼼北岸馆(秦皇岛),2025年,
图片致谢阿那亚艺术中⼼,摄影:孙诗
2020年,她与伦敦的柯芮斯画廊(Pilar Corrias)合作,今年也签约了老牌德国 Max Hetzler 画廊。选择画廊时,她尤其看重对方是否真正理解她作品背后的概念与文化语境。“他们看重的不是我的国籍,而是我的绘画本身。”她更愿意把自己看作一个不断打破边界,尝试新媒介、新空间的艺术家。哪怕是在传统的架上绘画中,她也试图通过展览设计去“激活整个空间”,引导观众以更近的距离、更身体化的方式与作品相遇。
当张月薇受邀去英国各地艺术学院做讲座或担任导师时,她特别向多元背景的学生传递了一种可能性:“你不一定是英国人,也能在这里做艺术。你可以留下来,并获得认可。”她清楚地知道——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地方,而是属于她经历过、吸收过、思考过也深爱过的所有文化之间那片流动的、开阔的地带。这是一只蝴蝶和她建立的世界地图。

张月薇《仿联体3》(Imitation Complex 3),
2024年,亚麻布⾯丙烯及油彩,220cm×190cm

“张⽉薇:地平说(Flat Earth)”展览现场,柯芮斯画廊(伦敦康杜义街空间),2024年
版权声明:除原创作品外,本平台所使用的文章、图片、视频及音乐属于原权利人所有,因客观原因,或会存在不当使用的情况,如部分文章或文章部分引用内容未能及时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或作者名称及原始出处标注错误等情况,非恶意侵犯原权利人相关权益,敬请相关权利人谅解并与我们联系及时处理,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创作环境,联系邮箱:236977919@qq.com。发布者:admin,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stm.com/news/1385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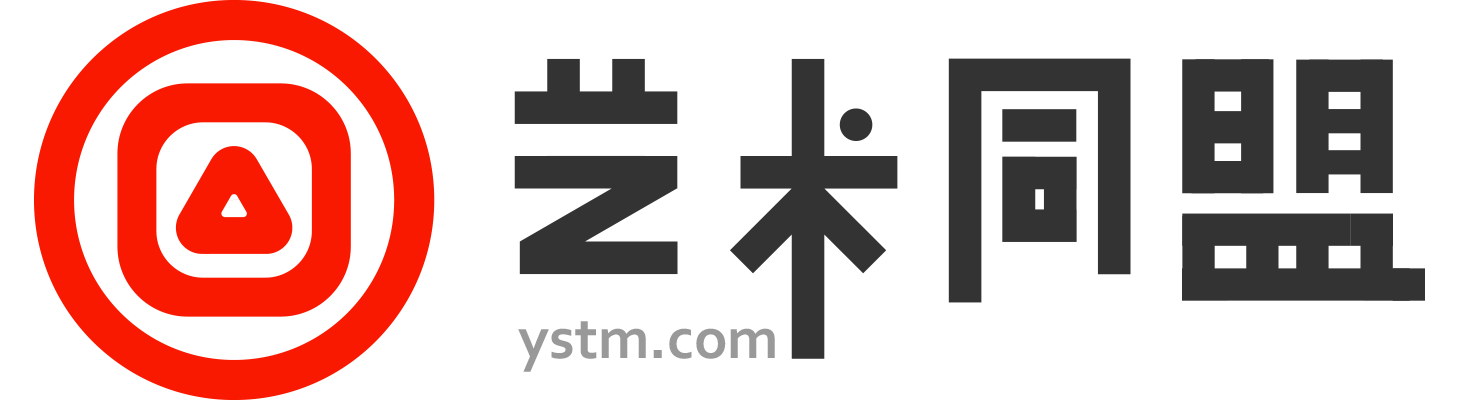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